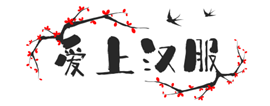穿长袍,何凡先生是理论家,我才是实行家。一袭在身,随风飘展,道貌岸然,风度翩翩然,屈指算来,数载于兹矣!不分冬夏、不论晴雨,不管女孩笑于前、恶狗吠于后,我行我素,吾爱吾袍,绝不向洋鬼子的胡服妥协,这种锲而不舍的拥护国粹,岂何凡先生所能望其项背哉!
长袍成为我个人的商标,历史已久,不但传之于众口,而且形之于笔墨。前年香港出版的一期《大学生活》里,某君曾列举台大的四怪三丑,而怪丑之尤就是“长袍怪”,好像长袍就是我的化身一般。事实上,若论台大声名显赫的人物,除钱校长外大概就是我了。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“文学院那穿长袍的”,除非他是瞎子,可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,除非他还愿意做聋子!
多少人奇怪我为什么一年到头老是穿长袍,可是我从来不告诉他们。他们恭敬视我,我低眉以报之;他们侧目视我,我横眉以向之;他们问我原因,我关子以卖之。教中国通史的夏教授也整年穿件破袍子,可是夏天最热的那一两个月,他也破例夏威夷一番。有一次他看我在盛暑之下仍穿着黑绸大褂大摇大摆,特地走到我面前,不声不响地盯了我一阵,最后摇摇头,不胜感慨他说:“你简直比我还顽固!”
其实我怎能算顽固?李鸿章穿缺襟马褂,比我还多顽固一层;入了咱们国籍的英国人马彬和,对中国“满大人”服装的倾倒比我还如醉如痴。只是台湾的天气热些,所以我显得比他们更艰苦卓绝罢了!有一次,一位颇有灵性的女孩子问我说: “李敖,我忍不住了,我一定要问问你: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,难道你不热吗?”我望着她那充满救世精神的脸儿.慢吞吞地答道:“冬天那么凉,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,难道你不冷吗?”这女孩子似有所悟,一句话没再说,黯然而去。我当时忍不住偷偷好笑,我笑她一定以为我在夏天的耐热和她在冬天的耐冷,出自同样的心理,其实才不对呢!女孩子冬天穿裙子,充其量不过三项理由:
一、为了美,为了满足她们的自炫心理;
二、为了阔,利用你的视觉告诉你她穿的是九十六元一双的玻璃丝袜;
三、为了优越感,告诉你她的脂肪含量比你们男士多,热情的人是不怕冷的。
可是我穿长袍在光天化日大太阳之下,理由却与她们迥然不同。盖穿长袍是一门失传的学问,降至洋服充斥的今日,凡是再穿长袍的人都有他一个深远的理论背景,我把这种理论背景归而纳之,分为五派,一统其名曰“长袍心理学”。
第一是“中学为体派”。此派可以钱穆为代表。钱先生承张文襄公之余绪,大倡东方精神文明,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他在行动方面,也表现出“中衣为体,西鞋为用”的精神–当然去美国时穿西装是例外,入境问俗,中国之进入夷狄者则夷狄之,何况圣之时者的钱先生乎?我个人在长袍一点上,足为国粹派争光。身外之物虽系小事,然“其意岂在一发哉?盖不忍中国之衣冠,沦于夷狄耳!”故我对它始终乐之不疲一往情深,时时玩索不已,心体力行不止,持久性足可追随钱夫子而臻于“汉唐以来所未有也”的境界。何况长袍还是我们东方物质文明最辉煌的表现,也是我们反抗文化侵略的一件有力武器,它那变形虫的特性给了我们无限的安全感,黄袍加身日,我思古人时。洋鬼子的物质文明又何有于我哉?
第二是“男权至上派”。此派可以某些女人痛恨者为代表。想当年清人刚入关,金之俊建议十从十不从,第一条就是男从女不从,所以当时男人穿清朝旗袍,女人穿明朝服装;到了民国后,男人又流行穿西装了,女人才流行穿旗袍。换言之,女人总是晚咱们男人一着,总是跟在时代后面穷赶,思念起来,好不开心!想不到好景不长,没过几年,女人们也穿起洋婆子的衣裳来了,但是她们并不喜新厌旧地放弃旗袍,反倒变本加厉,把旗袍开衩到苏酋黄的世界,而此世界之有碍观瞻与体统,不必多言一望便知。可是你又不能厚非小娘子们,因为她们这么做是有古书为之支援的,《诗经》上不是说过吗?
缁衣之好兮,敝予又改造兮!
有诗云可证,挟经典以重,老学究们还敢再多嘴吗?《礼记》中虽有“作……异服……以疑众,杀!”的王制,但是女人大可爱了,安能遽以一衩之高低挥泪杀之?何况普天之下率上之滨。双面夏娃多如牛毛兔子毛,又安能尽得而诛之?故劝千岁,杀字休出口,杀乎哉?不杀也!但是,既然不能杀之而后快,某些卫道之士自然不服气不甘心,但又恨无新服装可跟她们比赛。失望之余,只好折回头来,重新从箱底取出长衫儿,晒一晒,也穿起来了,心里还想:同是旗人之袍,娘儿们穿得,我穿不得?他妈的,穿!堂堂大丈夫奇男子,岂可让这些造了反的女人专美于前吗?于是“男权至上派”遂在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公愤下成立了。
第三是“招蜂引蝶派”。此派可以某些大包头型的海派学生为代表。这些暴发户的“太”字号们,到处横行,上穷碧落下黄泉,志在吸引异性的注意。但是女人是好奇的动物,不出奇安能使之好耶?于是大包头们纷纷出动,或穿黑衬衫、或扎细领带、或用妇人手帕、或喷仕女香水……千方百计,无所不用其肉麻之极,最后异想天开,居然动起他爷爷的长袍的脑筋来了。于是赶忙翻箱倒柜,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,只好找山东裁缝做了两件,又拿条花围巾,往黑脖子上一缠,俨然以北平大学生自况,真是沐猴而冠,望之不似人君,一看他那包心菜式的头发,咱们就够了!这些附庸风雅的无知之徒,其面目可憎、其黑心可诛、其长袍可送估衣店、其“招蜂引蝶派”可请少年犯罪组勒令解散之!
这四是“没有西装派”。此派正好与前一派相反,前一派因西装大多,尼龙、奥龙、达克龙……五颜六色,宽条窄条,穿得厌了,所以才穿长袍做同性而引异性;此派却因一条龙也没有;且西装之为物,日新月异,宽领窄领,三钮二扣,变化无穷,除非财力雄厚,否则休想跟上时代而当选服装最佳的男人。若穿长袍,就无这种麻烦了,大可隆中高卧,以不变应万变,任凭别人的料子龙来龙去,老僧反正是一龙也不龙,至多以聋报之。而且,清高的阴丹士林是从不褪色的,正如我们固有文化的万古常新,放之四海而皆准,俟诸百世而不惑,长袍小物可以喻大,“去蛇反转变成龙”,袍之既久,自怜之态砉然消失,路过短衣窄袖的西装店,反倒望望然而去之,只见他把咽下去的口水朝玻璃窗上一吐,仰天长啸曰:“予岂好袍哉?予不得已也!”
第五是“十里洋场派”。此派别名“职业长袍派”。即穿长袍和他的职业有神秘的关联。例如说相声的,不穿长袍就失掉了耍贫嘴的模样;拉胡琴的,不穿长袍就锯不出摇头摆尾的调子;监察院长,不穿长袍就不能表现出他那“年高德劭”的雍容。此外东洋教授、西藏喇嘛、红衣主教、青帮打手……都得在必要时穿起形形色色的长袍以明其身价。尤其是上海帮的大经理大腹贾们,他们的脑之满与肠之肥,几乎非穿容量较大的长袍不足为功。盖身穿西装,除了使他们更像喜马拉雅山的狗熊外,硬领、马甲、臂箍、窄袖、腰带等等对他们无一不是恐怖的报酬。本来西装就没有长袍舒服,西装穿得愈标准你就愈受罪,除了仅有“头部的自由”外,其他你全身的锁骨肋骨肱骨桡骨尺骨膑骨胫骨腓骨乃至屁股,没有任何一骨是高兴的。而这些重量级的好商巨贾们,由于脖子上的白肉大多,连仅有的头部的自由也被他们自己剥削掉了。不堪回首之下,他们乃相率在单行道上选择了长袍,除了可减轻桎梏开怀朵颐外,更可从林语堂博士之劝告,用”世界上最合人性的衣服”,来包住他们那快挥发光了的人性!李子述长袍心理学竟,乃临稿纸而叹曰:
昔孔圣曾有“微管仲,吾其披发左袄矣”之叹,管仲有恩于道袍,千载史有定评。从曹孟德割须断袍之日起,长袍遂有式微之兆。曹操死后一千七百年,华夏衣冠竟不幸沦于夷狄,自右衽而变中衽,自长衣而易短装,流风所被,长袍竟被贬为国家常礼服,且在裁缝公会会长眼中,俨然吴鲁芹所谓之“小襟人物”矣!岂不哀哉痛苦哉!余深信长袍不该绝,深愿我血性之中国本位者,于胡服笔挺之际,从速响应何凡之呼吁,以李敖为楷模,以于右任(“余右衽”)为依归。诗云: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!”千载袍风,此其时矣!三原有老,可同袍矣!此时不同,还待何时?寄语读者,快看齐矣!
小编按:李敖放荡不羁,桀骜不逊,学生时代就常以一身长袍漫步台大校园。十余年之前就有人提议李敖上节目穿汉服,但后来他再也没有公开场合穿过所谓的长袍,或是汉服。不少人认为他其实是反对传统复古行为的,其实在我看来,也许他并不是排斥汉服,只是过去主张传统文化回归的是文人,而现在推广主体是普通人,也确实是作为常服去推广了,且着装并不计较也没有真正的规矩可言,对于有血性的文人而言,这并非是一种合其道之路。在这篇《长袍心理学》文章里,也不免映射出当今人对汉服的穿着观念,亦有反思意义。换种角度,是该向先